简介
筱田正浩
池部良,加贺麻理子,藤木孝,杉浦直树,三上真一郎,佐佐木功,KôjiNakahara,原知佐子,宫口精二,东野英治郎,MikizoHirata,山本礼三郎,山茶花究,HideoKidokoro,AkioTanaka
剧情片
日本
1964
如果要为60年代的日本找到一个具体的象征符号的话,那么一定是戴着墨镜,穿着整齐西装,行走于茫茫人潮中的独行杀手了。从铃木清顺60年代的代表作《杀手烙印》开始,70年代今村昌平的《我要复仇》,80年代村川透的《该死的野兽》,这个形象在无数经典的日本电影中出现。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筱田正浩1964年的名作《干花》。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没有希望和生存目的的孤独杀手似乎正暗含着日本经历被占领时期后的压抑心态,同时黑帮杀手的浪漫化表现又重新呼应着日本传统文化中关于“责任”的命题。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仪式化的行动的展现。黑帮要求其成员绝对忠诚,同时,个体的公民向国家效忠,然而国家不需要,也不会报答公民的忠诚。在《干花》中,村上一次次为了组织杀人,即使这样他就必须失去自由,承受牢狱之苦。筱田给观众呈现的是宿命与受虐狂式的愚忠,黑道的义务折射的是被压制的情感表达和受限的色欲美学,“黑”之色彩稀释了冲动与活力的官能审美,所以我们看到了村上作为杀手的忍者般的生存状态,而不是007式的狂欢般的杀戮的娱乐。 回到关于“责任”的命题上,杀手有杀手的命运,老大则有老大的价值。《干花》中的老大,俨然一副慈父的形象,“早安”、“晚安”式的问候语让人仿佛置身小津的电影中。片中一个关键场景,老大提来两颗西瓜分给手下吃,自己则悠闲地给情人打电话,安排晚上的约会地点,要知道,此刻他的一位手下已经被敌对帮派干掉。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生活化的场景后,他才坐下来,轻描淡写地谈到关于复仇的话题,当有人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任务时,他还以“你有家庭”为理由拒绝了。当然,最终还是村上,这位孤独的人,还得再次为组织卖命。 有趣的是,看似反叛的新浪潮时期的黑帮电影却在有意无意地重复着小津式的关于家庭与责任的传统命题。也许是日本在经历了动荡的50年代后急需一种凝聚力来面对未知的未来,而黑帮的形成是基于经济的利益共同体,在《教父》中这是核心的戏剧冲突,但《干花》不一样,我们看不到一个关于“钱”的冲突场景(虽然电影中黑帮之间的角力仍然是围绕利益展开),即使是主人公要参加高额赌局,在他没有赌资时,向老大借钱,老大问了数目后,就再没有任何表示了(下一个镜头就是村上重返赌局)。那个来刺杀村上的年轻人也是因为之前村上杀死的人是他的好友,而不是其他的利益因数,后来他和村上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直至最终成为另一个“村上”。黑帮更多地被看作是无根漂泊者最后的归宿,它是种职业,更是种信仰,象征着团结和存在的目的。日本60年代黑帮电影受到美国黑色电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像筱田正浩这样的导演,他对大岛渚那种极端反抗美学并不感冒,而试图调和西方现代派与传统日本文化,所以在筱田的电影中日本变得极其“不确定”,除了夜晚闪烁的霓虹招牌上的日文,看不出这里和好莱坞或者曼哈顿有什么区别。内容上筱田也在追求某种“超越”,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本土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新浪潮的极端美学。 《干花》是一部异常奇妙的电影,它有黑色电影的外延,却保留了日本式的内涵,完美体现了筱田的创作理念。筱田曾表示“没有日本人肯为自由而死亡,但为美或者唯美化的纯洁而死则是非常日本式的行为”。黑色电影中的悲剧往往在于主人公盲目地对自由的追求,而筱田的独行杀手看重的不是自由,而是美,就像他的《心中的天网岛》,“心中”之原因正是美之极致的展现。村上最后自毁式的杀人,为美人,更为自己心里对完美的信仰。和黑色电影一样,筱田很好的解构了道德。黑色电影中的疏离与叛逆,放荡的女人和疯狂的男人,他们身上不再被附加上某种道德批判,在这一方面日式黑帮电影做得更加出色。筱田聪明地将主人公与社会本身隔离,我们只是影片一头(村上出狱时的上野车站)一尾(村上重回监狱)看到主人公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直接互动,在影片的其它时刻,我们的视角只会集中于主人公本身。这要归功于日本文化中的“私人”传统,从私文学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极其个人化的书写方式。 在前面提到《干花》的开篇镜头是在东京的上野车站拍摄的,这里是日本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主人公村上出狱时伴随着村上本人的独白,但其本人却被人潮淹没,影片中段,村上孤独地行走在大街上,身后的行人成为背景,这个基调正好与本片原著石原慎太郎的创作欲求相符。石原慎太郎文学中的主人公永远都是不融于大众的独行者,无因的反叛是他们的标签,并无时不在彰显着一种虚无主义的生活态度。影片开头出现了两次对鞋的特写镜头(火车上和赌场门口),之后我们才看到村上的脸,回归赌场是他重新获得黑帮身份的标志,而一出狱就直接回到这里,也预示着他的无所归依和宿命般的结局。 在影片中非常重要的几场赌场戏中,观众可以看到筱田冷酷、迷人的黑白摄影,虽然我们并不懂得日本黑道中流行的这种花牌赌博的规则,但配合着影片的精彩剪辑(赌徒们手的特写、翻开的牌的特写、脸部的特写)以及武满彻精彩的配乐,观众完全能走入到主人公此时的心理状态中。《干花》的配乐在西方一些影评人看来可以算是当时最大胆、最前卫的电影配乐了。这完全要归功于武满彻这位日本电影的传奇配乐大师。筱田正浩、大岛渚、吉田喜重这些新浪潮巨匠与武满彻的私交都非常好,在《干花》中,武满彻甚至直接参与了影片的剧本创作、外景选址和具体拍摄工作,这完全超越了电影配乐本身的职责。武满彻找来交响乐队配乐,但又在录音室对其进行了失真处理,这让观众最后完全听不出来这些奇怪的声音究竟是由哪种乐器发出的?《干花》中被人津津乐道的赌博场景中,花牌本身是使用及其坚硬的纸片制作的,在洗牌时会发出“哗…嗒”的明显声响,武满彻发现这种声音很像跳踢踏舞时会出现的声音,于是就请了当时日本著名的一个双人踢踏舞组合来录音。在影片中,真实的洗牌声音逐渐过渡到踢踏舞步的声音最后到那失真处理过的精彩配乐,情绪一步步变得饱满,气氛也变得更加紧张。 《干花》的令人难忘之处就在于它的意乱情迷般的疏离感。这种“冰与火”的完美结合让观众欲罢不能。村上在赌场结识了神秘的女人沙耶子,被她的孤独气质所吸引,而沙耶子的形象取代了之前新浪潮中反叛、虚无的男性主人公所代表的沉郁主题,她更像是沟口式的女性角色的复活,是被“政治化”的女人。外表迷人,行为疯狂(参加大额赌局、玩命式的飙车),麻木(从不主动表露情感),绝望(眼看心爱之人的毁灭),空洞(吸毒、自毁式的死亡)。沙耶子与村上关系的递进在西方评论家看来是施虐--受虐的潜文本,我觉得更像是日本战后疏离一代的自白书。他们不再相信某种永恒的东西,向往自毁式的物哀美学,又无法把握生命瞬时性的稍纵即逝,对欲望的抗拒(赌场被抄,两人假扮情侣,村上本有机会吻沙耶子,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知道对欲望的放纵就是悲剧的开始。 筱田在《干花》中对当时日本面临的严重的毒品问题进行了批评。在村上的梦中展示了他的恐惧。在河中无助的漂泊是对无所归依的恐惧,无处可逃时所打开的门却又进入更深的黑暗之中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村上回到监狱的镜头与这儿惊人地类似),看着女人沉迷毒品是对失去爱人的恐惧(村上在监狱中得知了沙耶子的欺骗和她的死讯)。影片最让人吃惊的场景来自结尾处的暗杀。为了告诫沙耶子不要触碰毒品,村上要向她提供更强大的刺激--观看他杀人。此刻的场景却变得异常温柔,激烈的配乐变成了英国宣叙调大师柏塞尔的《狄多和埃涅阿斯》,柏塞尔那无以伦比的经文歌式的合唱以火热的激情把悲剧推向高潮。走上黑暗盘旋楼梯的村上,天使雕像的特写,和站在远处白光中的沙耶子,她就像守护天使一样在陪伴着村上走向那极致的毁灭之美。 《干花》在横滨拍摄,主要的外景拍摄场地是在一座废弃的红灯区,极具破败美学风格。这让我们联想到黑泽明的《天国与地狱》(同样涉及毒品问题)。这座在当时最具西方气质的城市,在筱田看来却也带有最多的日本传统印记。在影片中的一个场景里,村上来到前女友家(一家钟表店),屋中挂满了时钟,武满彻让时钟的“滴答”声成为完美的背景音乐,筱田在这个场景中为我们展现出此刻正处于美、苏冷战夹缝中的日本,它正迷失在时间的迷宫中。更加具象的是影片中没有一句台词的来自中国的杀手小姚,他冷静、英俊,酷到令人窒息,这是筱田的隐喻,一个更加神秘的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它会怎样影响日本?是暗夜里突然射来的飞刀?还是让人无法抗拒的毒品?我不能肯定这个角色的真正含义,但看完这部电影,我猜测这将是一个持续着的寓言,关于一个孤独的人如何能在一条充满了陷阱的路上走下去。我想,这就是《干花》的主题吧。
@《干花》相关推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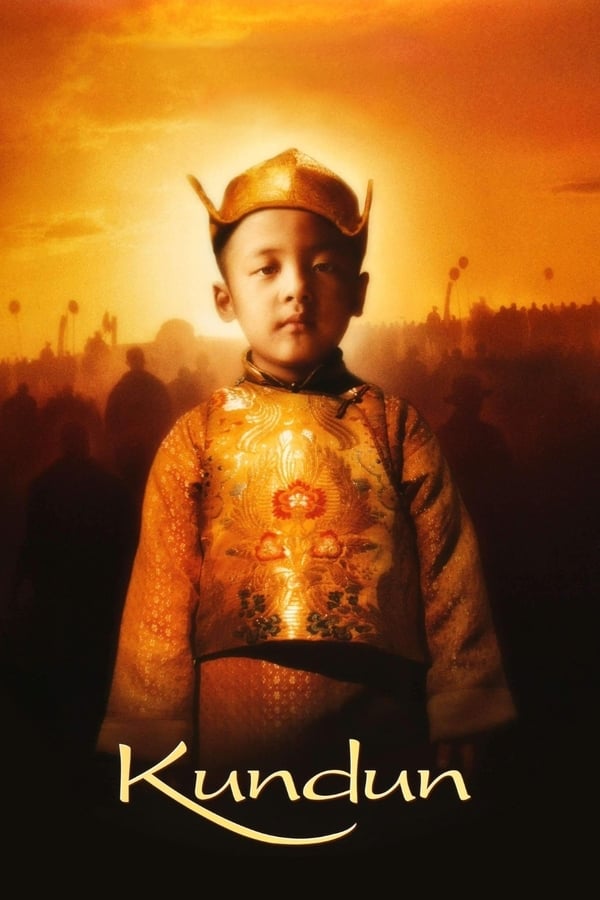 HD
HD
达赖的一生
内详
-
 超清
超清
海林都
张熙唯,关楚䆣,高伊罕,图门巴雅尔,昂和尼玛
-
 HD中字版
HD中字版
拉努埃大街
霍光,卡梅丽雅·乔丹娜,XunLiang,MauriceCheng,XinglongZhao,QiqianXie,ZhiweiRen,TienShue,WabinléNabié,XingXingCheng,SimiaoYang,JingshuaiCao,YilinYang,Jung-ShihChou,伊冯·马丁
-
 HD国语
HD国语
卧底1992
王诗槐,王卫平,周笑莉,舒适,曹秋根,严荷芝,张小亲,阙云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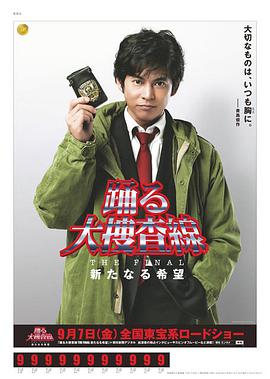 全4集
全4集
跳跃大搜查线最终篇:新的希望
织田裕二,深津绘里,柳叶敏郎,中山裕介,小泉孝太郎,小栗旬,伊藤淳史,内田有纪,香取慎吾
-
 HD
HD
龙门飞甲电影版
内详
-
超清720P
婚礼之后2006
麦斯·米科尔森,NeeralMulchandani,罗夫·拉斯加德,西德斯·巴比特·科努德森